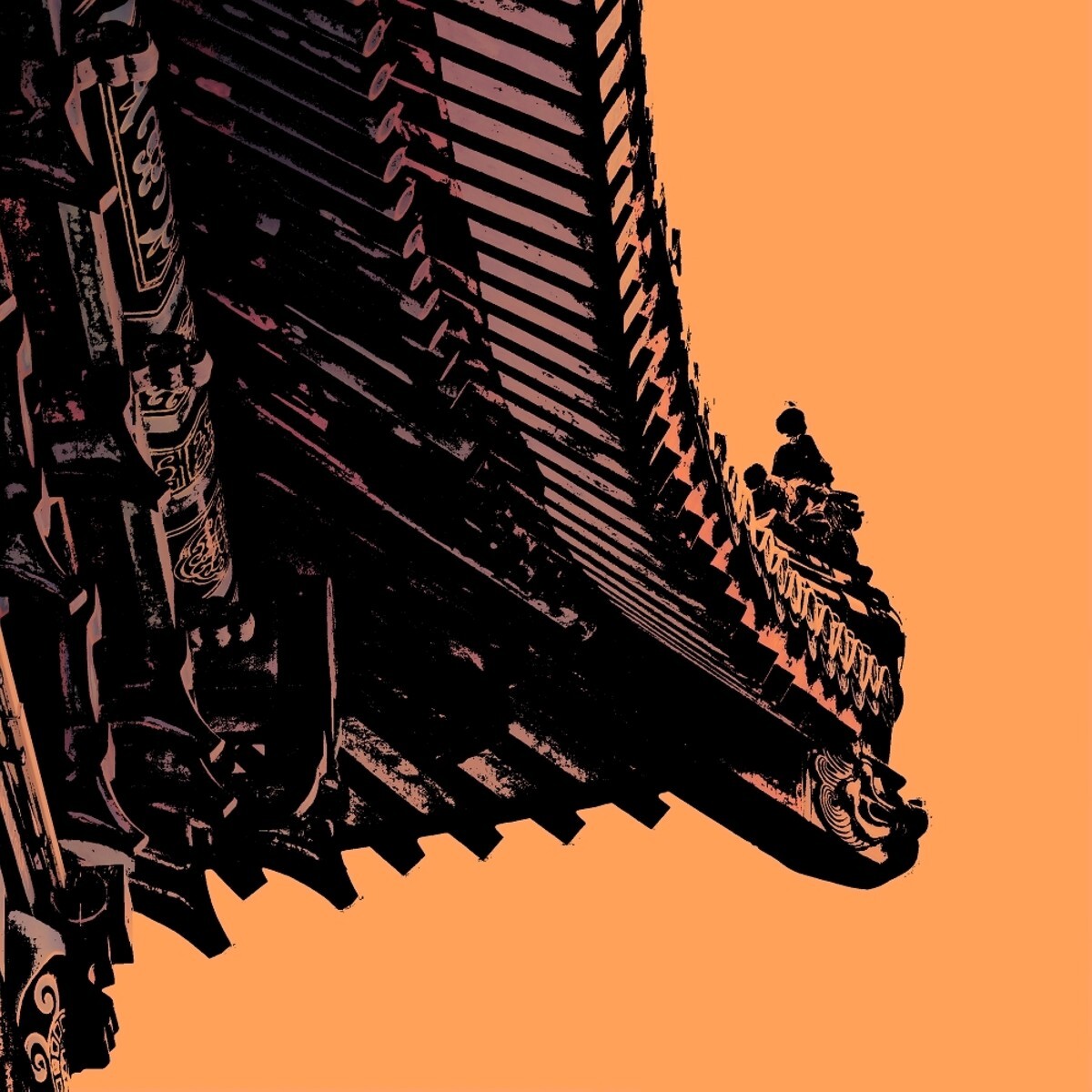
大上海计划,不单是造几栋楼那么简单,它是民国意志的觉醒。
上海市通志馆,上海通社,“征信录”, 上海市第一本年鉴都在那个时候风起云涌。
“通志”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可以是一个朝代的通志或地方通志。通志馆便是编写存放通志的场所。《通志》较早的起源应该早于南宋郑樵所著的《纪传体中国通史》,《史记》之后,《纪传体中国通史》为现存的另一部通史巨作。
1932年,党外人士柳亚子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负责编撰第一部上海市志,“全书假定二十五个门类,二百几十个总目,六百几十个子目;字数至少在二百五十万言以上”。
至1937年《上海通志》第一编《沿革》和第二编《公共租界》虽未付梓,但还是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两本《上海研究资料》。
“报纸副刊、保藏不易;倘有遗漏,补置尤难”。1934年上海通志馆以原班编辑部成员成立了上海通社。
“通”:通晓、精通上海凡百事务;通社从“上海市通志馆”馆名另出,暗示二者两位虽有公私之别,实为孪生姊妹。
开篇《上海通》在《大晚报》副刊上开始与读者见面。
上海通社《老上海》版在《时事新报》上开了每周一次的见面;
1934年,通志稿文字已经完成一半了,按这个进度1935年完稿应该是没问题的。但馆长是领国民党薪水的,专业人士很聪明的要为通志馆的长期生存谋后路。 “因为年鉴是每年要出的,只要年鉴一年一年出下去,通志馆也就可以因此而长期存在。”况且“通志完成以后,需要有一个机构把上海新近发生的事继续记录下来,为今后的编志工作打好基础。”
上海第一本年鉴,在聪明人的运作下诞生了。
1936年《上海研究》又在《民报》上出半月刊。同年,上海通社决定择其中重要篇章集印成书出版《上海研究资料》。
1939年《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出版,这两本书集结了上海通社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是研究上海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1984年和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先后将其重新影印。“虽则零星、简单、软性的,我们都不愿说废话和空话,希望能做到语必有据”
“征信录”为当年一些手工业公会、商业工会及其他同乡会组织每年做的账目,它真实的反映了一个组织表甚至一个行业的经济状况。若干年后有不少就散见在各地摊上,1936年通志馆人员将收购来的原始凭证编了一本《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第一号:征信录目录》。
“有些稀有的书,甚至是未刻的稿本,应当设法把它们印行,以广流传,供大家研究,以免万一散失,永不能弥补”。
民国24年《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十册出版,《沪城备考》《淞南乐府》等14种书名列其中。第二集《云间志略》等7种因经费问题未能出版。编写市志,理应可以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索取资料,但在当时这是不可能的。 “如有关于上海之掌故等稿件者愿义务供给于《上海通》丛刊者,请寄上海萨坡塞路上海通志馆转交上海通社为荷”。
今天的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是否也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面来这样一段小广告呢?